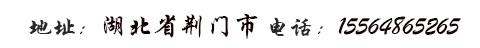新荷人才飞廉写诗,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
|
飞廉 本名武彦华,年生于河南项城,毕业于浙江大学,著有诗集《不可有悲哀》《捕风与雕龙》,与友人创办民刊《野外》《诗建设》。 年获《江南》“首届江南诗歌奖”提名奖,年获《诗刊》“陈子昂青年诗歌奖”,参加第33届“青春诗会”。 写诗,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文|王亚琪 “前望舒使先驱兮,后飞廉使奔属。”年,武彦华18岁,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,叫飞廉。与戴望舒的望舒一样,“飞廉”取自屈原《离骚》中的同一句,在中国古代神话中,是“掌八风消息,通五运之气候”的风神之别名。那时候的武彦华没有想到,这个名字一用就是25年,伴随着他从辽阔旷远的中原大地,一路来到了杏花春雨的江南。而他笔耕不辍写下的几百首诗歌,也沿着历史悠久的地域长河,在年复一年如切如磋的打磨中,逐渐展现出珍珠般的莹润。 从南宋古皇城遗址的坐落地凤凰山,到漫天卷地气势磅礴的钱塘江,再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,这些年来,武彦华的诗像是在跟着居处不断更新,山水景致、人文历史,每到一处,便总有诗文相应。尽管在朋友眼里,武彦华从小到大都是那么才华横溢——他是少年时就能以诗歌对文的才子,信手写下的情诗能襄助同袍求得窈窕淑女;他是青年时的隐士,凤凰山上时光易逝,八年山居生活让他写就锦绣辞章,声名远扬。“我想这是天生的吧,关于写诗。”武彦华说,这就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,也必将会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 而这所有的一切,在二十二年前武彦华来杭州求学时的那个夜晚,或许便早已注定。那是西湖边的荷花都已谢尽的时节,有一个少年与他的挚友来到了苏小小墓边,彻夜长谈。从此,江南对于他不再是诗句中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这样模糊的想象,李贺、李商隐都写过的苏小小,也仿佛在某个特殊的时刻朝着千年后的西子湖盈盈地转身回眸。“我相信当你对某一个地方的历史有所把握后,所感受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。我熟知脚下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过往,这就像踏入了另一个时空,让我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了奇妙的结合点。” 武彦华说,在凤凰山上住的这些年,他甚至恍惚间觉得,自己是从南宋存活至今的遗民,他也的确像那古代最勤奋的书生,写一首诗常常便要斟酌上数年。“诗歌就像是一件最完美的工艺品,不同长短、不同尺寸的木料是做成一把琴还是一张凳子,都要经过诗人的设计和规划。”年武彦华写下《马六甲海峡》,中间历经十五年,才终于完成。“有时候可能是几个字,有时候或许是几段词句,总归是要磨的,你的想法也在不断地变,这就像心中埋着的念想,一个闭着的盒子,直到某一天咔嚓一声,你便知道,成了。” “但我并不信赖灵感。我更相信写诗是要靠努力靠积累的。”武彦华有一本自己做的字典,将自己读到的所有他认为可能会对写诗有启发的字词、诗句、名称都记录在册,它可以是某一种绚丽的颜色,也可以是某一类植物的名字,还有可能是一件有趣的新闻。“比如我曾听到的一个有意思的事,说的是有一个人总会在喝醉酒后,就爬上山去采药。我便将这事也写进了诗中。”在他看来,人一辈子能写出的好诗不多,而往往那些写就佳作的瞬间,都需要那么一点运气与机遇。“我或许成不了李白、杜甫,但我希望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,即使,只是向我所崇敬的他们致敬。” 本文来源:《青年时报》 本期责编:王瑾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ehuaf.com/hhzp/5982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荷花社区丨新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助力文明城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