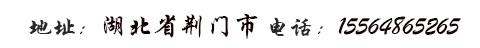高邮文联校园文学社风采一颗文学的l
|
北京专业治疗白癜风医院 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C%97%E4%BA%AC%E4%B8%AD%E7%A7%91%E7%99%BD%E7%99%9C%E9%A3%8E%E5%8C%BB%E9%99%A2/9728824?fr=aladdin 一颗文学的“新苗” 陈疏桐 前 言 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,校园文学置身于校园,根植于纯粹而又美好的校园生活,展现着青春特有的光泽和活力。这些文字或许稚嫩、或许青涩、或许简单……但却埋下了一颗颗必将成为参天大树的文学种子,江苏省高邮中学《新苗》文学社便是一本埋下种子、培育新苗的刊物,《新苗》创刊号中这样写道:“一棵棵有志于文学的‘新苗’浴着时代的晨光,破土而出;一群群少男少女带着童话的梦幻,悄悄地叩响了通向文学神圣殿堂的大门”。 人/物/档/案 陈疏桐女,高邮中学届文科竞赛班学生,年以高邮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曾任《新苗》文学社30届编委会副主编,爱好文学、始终如一。高中时曾获得国家级英语能力竞赛一等奖、省级作文竞赛、科技竞赛一等奖,个人作品在《美文》等杂志发表。参加北大史学夏令营,并荣获江苏省“三好学生”。 人物语录 钟嵘说:“嘉会寄亲以诗,离群托诗以怨。”奈都夫人说:“用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。”荷尔林德说:“诗人是酒神的祭司,在神圣的黑夜,他走遍大地。”诗、文、史,乃至整个人文学科,都是人类灵魂的宿处。它让人类多变而细腻的情感找到了发泄的豁口,让罪恶找到了救赎之道,让整个人间有所期许,生机如林。我愿意流连于这气象磅礴的世界,眼观古今之事,热情饱满地过活。亦是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 陈疏桐作品欣赏 秋来 久滞幽州意索然,西风未烈叶仍悬。 归愁难耐起行桨,猿啸不堪惊客眠。 潮落寒江斜照里,蛩鸣霜木素芦边。 明朝烟雨瓜洲渡,且进杜康鲈鲙鲜。 江城子·秋 水晶帘上映曦光,倦拢裳,意徊徨。一夜凄风,积雨浸阶凉。槛菊枝疏花影瘦。人不见,对空堂。 深情自古未曾长,梦鸳鸯,付黄粱。望断朱墙,唯有雁栖梁。料得年年新殿处,添橘柚,试时妆。 点绛唇·览镜 午梦初醒,慵闻莺啭疑为雨。杏衫轻舞,临镜梳云缕。 螺髻香腮,栀子芳心吐。花面妩,见吾如许,也应羞无语。 趁未老,尽疏狂 ――评《明清性灵》(邱江宁著) 夕照橙黄如橘。 最后一页缓缓翻过。胸中浊气荡涤一空,如站在河边闻着新涨的春水味儿。 明清之际确乎是有推崇“性灵说”的传统,但邱君并不局限于此,她将性灵的观念推而广之,用以形容一种至真至我的处事状态。所选数十篇,皆状性灵之人,他们顺遂真意,举止灵动,旁若无人、独抒性灵……令人观之而生向往之心;所写之事,皆摹性灵之事,弹琴饮酒、煮茶赏花、雪中观亭、山间遇雨……令人读后而欲从其事。 若言自处,当如李贽。 自处,即反观内心、回到自我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在《李卓吾先生遗言》中李公以戏谑的笔调交代了身后之事,如何裹尸,如何挖坑,如何立碑。句句看似肃然却掩盖不住调侃之意。读之可想见为文心境:尔等儒学大宗讳死,我李贽偏不畏死;尔等以我为异端,我死之日,也不奢求认同,若非真情,不许守墓,不羁之气流露。卓吾一向如是。理学横行的年代,他不甘湮没于大流之中,不甘戴上虚伪的假面,偏不代圣人立言,只代童心立说。明知道自己著书的结局,非焚即藏,却也高傲的走着属于自己的路。 若言与天地相处,当如张岱。 与天地相处,是自然对心灵的净化,更是自我与自然的契合。极纯极静的《湖心亭看雪》勾勒了百年前的那个雪日,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,一痕长堤、一点湖心亭,足让陶庵欣然自足。于他,天地并非是冷冰冰的物象,每次踏入自然都是一次心领神会的对话与自我回归,油然而生的是最初的惊喜与感动,他会为未能拜访家在西溪的友人而久留遗恨,会为在酣眠西湖荷花中而深感惬意。 若言与人处,当如震川。 与人处,须怀一颗慈悲心。《寒花葬志》寥寥百字,催人泪下。状妻子婢女寒花,如在近前,“曳深绿布裳”“目眶冉冉动”,令人心生怜惜。后笔锋一转,“奄忽便已十年”使人猛受一击,感同身受,默默然。归氏素来文笔简淡如斯,“不事雕琢,却自有风味”。心念先妣,则大呼:“世乃有无母之人,天乎?痛哉!”;思念亡妻,则黯黯然,久视如盖枇杷树。归氏有如此风格,绝非刻意而得,实乃天性表露。他鄙视“入门而私其妻子,出门而诳其父兄”的自私小人,而推崇人出生之时“不知有彼我”的单纯真情。真情待人,犹如稚子。 见自我,见天地,见众生。见过自己,知道自己的分量,见过天地,知道自己的卑微,见过众生,方才修炼了一颗慈悲心。此刻,疏狂亦是慈悲的表现。 然今日性灵何在?罕矣! 那终南山上早就没了隐者的踪迹,田间路上也再无骑驴狂歌之人,散花洲上亦没有青箬绿蓑的渔父。 古之人自幼浸润宗教教化之中,形成如玉的品行与近乎完满健全的艺术心灵,长大后趋向于美,趋向于善,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今日之人,连最基本的美学教育也不足,于是乎,对于美朦朦胧胧。起心动念,无非蝇营狗苟。更可悲处在于,纵然有性灵的火光,也会招来群众嘲弄与讽刺,炒作与利用。世风日下可知矣! 邱君著此书,无非是大声疾呼,点醒梦中人耳。如萤火一般,去照亮一个个灵魂前行的路。 如此,亦会有“当代性灵”的存在。 过阴天 夏日沉重的墨云翻卷了一方天空,整个城市的光线暗下来。空气压抑而湿润,而风却不凉爽,恼人的、黏黏的热着。 清和回家时,家里空无一人。 我们今天吃面哦,念真。清和心里想着,嘴角漾开大大的笑涡。 多年生活在大城市,她与他,繁中无暇,已早将面等同为泡面,且食泡面时并不多,多在纪念什么,如仪式一场。 拧开水龙头,水气以溢散的方式扑面而来。盖好电水壶盖,插上插头,欲开不开时,丢入泡面,水与面过一会儿便一起湿热感人起来。细细捞出,有的条条尚沉于底,以筷触之,如河底鱼,惊而欲逃,追之愈急愈不可得,便笑。入碗,两碗分开,按序倒调料包,以壶中水浇,即成。清和不是很喜欢过多的仪式,但是心中有纪念,日子就被添上了不一样的注脚,于手上自然舒缓。 窗户呜呜作响,风大起来了。树木的辫子被曳住,伸长,变形,怕是要下雨。 清和想起来,小时候过生日奶奶总要下阳春面。厨房里水汽粘黏于窗玻璃,暮色蓝中杂灰,温柔地包裹了一盏厨房里的黄光。面算不上多好吃,加个蛋,大家一起纪念一下几年前的第一声哭啼。黄光照亮了棕黑的面卤,使它有了流动感,热气腾上来,迷蒙了灯泡。散落的花椒外红而内黄,辣感逼人。 清和抄起筷子,又笑了。念真与他初见时,由于紧张,忘了掩饰自己,拿筷子只捏大头、像用镊子的坏习惯。两根筷子张得老大,筷头油汪汪,嘴边一粒芝麻。黑色圆框眼镜,傻气的雀斑,一脸正经和故作深沉。那天吃的冒菜,筒骨汤料就白菜,外加一块泡面。念真扬言要开一家冒菜店,在年老时,开到西藏去,高原更需要热气腾腾的东西呀。养条狗,就叫念真。 清和去找芝麻和花椒,打开柜门,竟有几只蛾子探头探脑地飞出花椒袋,芝麻也泛青黑,霉了。真是不巧呵。 这时,他顺便瞥向窗外,树收敛了些,而雨确乎是白花花地涌下来了。 清和捞完最后一点料,埋头喝了几大口汤,顺手将念真的那一碗放在窗口。“念真,三年过去了。”清和的眼底深邃,透过镜片映出忧愁。一个人过阴天,总是忧愁的。 念真生前常说年少绝症,极怕死亡,而最怕被遗忘。但人几十、几千万年总是会被忘的,真是忧伤。 或许,纪念日能挽救一些,让生命不至灰暗到死寂。清和轻轻地说。 他望见远方有一只白色的鸟,它越过茫茫雨帘,盘旋哀鸣,它的羽湿了,它的喙湿了,像一张刚洗的白帕子。它最终落在清和的屋檐下,不言不语,蹙然有思。 清和推开窗的那一霎,它的眼神,像极了女子。 安魂 初雪降临到这片乡村的土地上。上世纪庞大而笨重的石碾、松柏仍青的坟堆一律淹没在白沙一样纯粹的雪中。万物失了色,天是冬天里常见的水泥灰。韩雀从后窗看到,白杨枝上落了不浅不厚的白羽,细细黑黑的枝条剪纸一般熨贴地粘在天空边。竹架上的紫藤正呈现出一种草堆的老黄色,像秃了头的老翁,像杂乱的鸟窝。被雪盖住了,隐隐有淡淡的烟在腾起。 老式瓦屋檐下悬了一排水柱,衬着白雪,它们倒是白的了。由于朝暾的加热,有的“嘎”一声整个的断掉,有的“叮”一声断了小半截,还有的“吧嗒吧嗒”滴着圆润冰凉的水。 奶奶肥胖的身子圈了一个大的烤篮盆进来,那印着“”的有着龙凤图案的盆热腾腾地冒着水气。她“咣”一声将盆置于床头柜上,韩雀不由地一惊。她撸上两边棉袄袖子,去捞里头的毛巾,嘴里嘶嘶地嫌烫。细细捏起一头,缓缓地把那端提上来远离水面,在空中前后一摆,然后使劲地挤出毛巾每个毛孔里的水,最后像摊大饼一样摊在头上,在腰上揩了热乎乎的手,沿着床边坐下:“今天有味口?煮了大米粥,也下了汤圆,爷爷已吃过上班去了。”韩雀只是心上不舒服,空空痒痒的,连句话也是蚊子哼似的挤出来:“不想吃,一点不饿。” “咦——,”奶奶头上有白气袅袅,“成仙了。四五天就沾点点饭,呆呆的也不出去玩。怕是病喽。”奶奶说着就来摸韩雀的头、手,“头不热呀,手心跟冰块似的。鼻子酸不?”韩雀往被子里缩了缩,“懒得动。”正说着,又抖了一下。他觉得烦,又说不出烦什么,头、手、脚都虚飘飘。于是就像奶奶说的,呆呆地向后窗看去,反正没啥意思。 “我晓得了”奶奶静静地想了一会儿,“前些天晚上你从韩山山家回来可是被王胡家的大黑狗猛不防一吓?你那天家来就呆愣愣的。”韩雀“呜”了一声,“怪不得这几天总心怕怕的。”奶奶取下手巾换了回水,复铺好:“小孩子家魂儿还不齐备,胆量小,不稀奇被吓到。你等下。”韩雀疲劳地闭上眼,奶奶从柜屉里翻出一块钱,一面小镜子。拿钱一下下在镜子上掂了掂,三次,硬币立起来了。它丝毫没有要倒要晃的意思,在寒气中闪着诡异的光。她嘟嘟嚷嚷道“可不是吗,这就讲得通了。” 奶奶替韩雀掖好被角,“乖乖莫怕,奶奶替你叫一下魂。韩雀第三次抖了一下,他信奶奶。 奶奶拉开门,一片白光清冷地映在地面上。出去不久,捧了一个生鸡蛋进来。她迅速地将鸡蛋麻利地立好在写字桌上,有如神助。这一套流程像一项技能似的,奶奶做得十分娴熟。她眯上眼,整个脸的褶子都起了,像韩雀揉皱了的纸。她凝视鸡蛋的眼神就像温柔的老猫注视着满含生的希望的小猫,像虔诚的基督徒观望圣人的油画。她轻轻地又坐到床沿上,小声嘱咐韩雀:“莫讲话哦。” 她一下一下拍着床边,“小雀儿回奶奶这,小雀儿回奶奶这,小雀儿回来睡觉。”韩雀望见屋檐下有几只麻雀飞来,格格笑了起来:“我是你们,你们也是我。”奶奶的声音低沉婉转,穿过庭雪的小孔,越过墙头,拉长了,拉长了,在雪野里回荡。大黑狗“呼呜——”地哼了一声,没精神、愧疚似的窝进狗房里。“莫怕——莫怕——”韩雀觉得奶奶在唱歌。不自觉地他睡过去,又不像睡过去。一个人似魂体分开,魂向上飘啊飘,飘上了房顶,飘过了瓦屋,看见了整个庄子,甚至可以看到紫藤的根在呼呼大睡。像睡在白云上,轻柔柔的,没有声音,大地静默着。手开始麻酥酥,有如千万只蚁虫疯狂蠕动。弯一下食指好似有了些力量。他又感到自己沉沉向下坠,很快地坠到了床上,安稳了,出了一身汗。 猛一睁眼,金色的阳光绢帛一般撒在床上、被上。奶奶瞧见,忙从保温桶中拿出熟鸡蛋,一摸他后背:“好啦,出汗了。”他张了张嘴,一阵冷气擦着嘴唇而过,他突然觉得嘴唇干涸的要命,而胃却确实因缺乏油水而焦灼。蛋白下肚,头脑渐渐和暖起来。奶奶点点头:“这就好了,你再睡睡吧。” 午后滚热的阳光映得玻璃一片刺眼的光,在这光芒里,一切就像做梦似的。奶奶坐得久了,一站两眼一黑,她下意识扶住了床头柜。韩雀突然觉得,奶奶的背影是那样苍老。他在想一个问题,等他自己六十来岁时,谁给他叫魂呢。 竟有些惆怅,小小年纪。 十里红妆 夏日里头,家家户户的栀子都打了苞,朝暾中半梦半醒。桥头路边的甜气浮在青色的雾里,浸润江南婉约的眉眼。迎亲队伍来了!村头的阿黄、小黑摇摆着尾巴、撒脚丫子朝着马蹄声奔去,青石板路上洒下一地清脆之声。他们也是通人性的,叫声饱含着欢欣与愉快。炮仗放过,新娘垂泪再拜爹娘,被扶上轿子。一干人马,花花绿绿映在水中,浩浩汤汤上了路。且不说那三等花轿由大而小、气势参差、依次而列,也不必说那宝镜缨络、垂丝花穗摇摇摆摆,单是那木雕人物就足以引得村中小孩儿寸步不离、相随而观。上了金粉的木雕在太阳底下带着底气十足、富丽堂皇的金光,宛若极乐世界的庭台楼阁。薄而起伏的是绿水,羲之站在一旁笑眼凝视爱鹅;柔而连绵的是大漠,昭君怀抱琵琶、身姿窈窕。仍有《牡丹亭》,《西厢记》,三国水浒,活脱脱就是皇家戏台。数不清的是良辰美景、赏心乐事,道不尽的是如花美眷、神仙伴侣。花轿的前后围了一圈送亲队伍。出了村,到了大路。吹号的吹得越发起劲,敲鼓的敲得越发欢快。发糖的脸上抹了红澄澄的胭脂,上扬的嘴角已盛不住笑容,专拣小孩孩送糖。撒玫瑰牡丹的花娘头上戴了一圈绸花,动作娴熟而不紧不慢地将花撒向人群与路旁的大河。空气里香腻腻的像卖糖人的刚来过。路行至半程,最后一箱嫁妆才刚从娘家出门。路旁茶楼上的客人看的呆了,上来的龙井,愣是半晌没理会。卖烧饼人家十六岁的大姑娘,弄着乌黑麻花辫,娇娇然倚着门欣羡地望着美若天宫的花轿儿走过。上学的哥儿们在拐角处奔出来,心照不宣地唱开了:“新娘娘,美娇人……”被箍桶的老妈妈瞪了一眼,“去去去,皮死了。”新嫁娘一身红端坐在轿中。盖头绣的是龙凤呈祥,上衣绣的是鸳鸯春暖,手帕绣的是麒麟送子。玛瑙珠穿成的链儿悬着金锁,朱红色玉扣在左手上。新嫁娘见不到外头的景,只听得锣鼓声、喧闹声一路上一阵高似一阵。江南女娃娃一生最欢喜的就在今日了,十里红妆,送嫁人一路逶迤。但是不知怎么的,她忽然有些凄凉,有些伤心。场面越盛大,父母亲出的心血就越多;旁人的祝福越多,父母的落寞就越深刻。一路欢歌,一路莺语,江南父老的淳朴她记在心里了,父母的劬劳她也记在心里了。她多想捂着脸嘤嘤哭泣一番。这时,一声鞭炮炸开了。已经到新郎家。帘儿撩起,该下轿了。生而为人 海棠不惜胭脂色,独立蒙蒙细雨中。 阿诺起身拉开窗帘。 惨白的日光灯映在深海般胶黑的夜色里,院中,垂丝海棠像人一样,显出老态。 下雨了,这该怎生是好。 曾祖父去世已有一段时间,明天正是烧纸房子的日子。可是今儿傍晚天却不给面子,滴滴答答下起雨来。 巨大的纸房子正停置在堂屋中央,极高的顶几近于屋上的木梁。堂屋华丽金黄的光反衬出诡异的蓝色,微微的风吹动纸门,沙拉沙拉。爷爷奶奶围着纸屋,神色欣慰:这屋气派得狠! 尽管才20岁,但阿诺似参透一切,对于死亡少了些畏惧,多了几分悲天悯人的意味。人生在世,如白驹过隙,忽然而已,不可说,不可说。 她带着悲伤拉着身旁妹妹的手,携着青年人独有的忧伤,深情望着那庞大的屋子。 纸屋的风格是中国传统样式。鳞状纸瓦密密麻麻码在顶部,仍有雕龙飞凤,长鸣其上。似是皇家阁苑,蓬莱神宫。往下是两页洞开的大窗,向里看,可真真惊奇。纸叠的炉灶稳稳当当地承载着一口小锅。灶下有红纸冉冉飘飘,真似雄火灼灼。精美的纸床、纸桌等,那般精致,不像是祭奠亡者,到像是小娃过家家的物什。 中国人对亡者通常怀着一种大悲大哀、大痛大挽之情。对于阴间的笃性,让我们怀着最最质朴的心愿,愿为最亲的亲人送上最后的祝福。 表妹露出惊惧而不满的神色:"姐,别看了,什么神啊鬼的,都落后了,迷信。” 阿诺握紧她的手,不言语。 灯光耀耀的金色让她想起多年前,曾祖父窝在藤椅上为清明节折金元宝的那些午后。那时院中海棠正盛开,以摧枯拉朽之势占据了树枝的角角落落。那时春风正柔,家庭和美,四代同堂,其乐陶陶。 极端失水的皮肤裹在瘦弱的指骨上,暗黑的老人斑耀武扬威地盘据了手心手背。微微颤动,从蛇皮袋中用指甲抓出几张,倏尔一抖,险些掉落。用长指甲捻开一张,无比缓慢而深情的五六折,金色元宝便成了。将其扔入另一个蛇皮袋中,口中默默念着以记数。 这样浩大的工程通常要持续一周左右。 一周后,迷离温吞的春阳下。曾祖父失水橙皮般的脸上会绽开了朵朵菊花,他左手扶着拐杖,右手颤巍巍指点着几个蛇皮袋:这是给谁的,那是给谁的…… 阿诺听得仔细而专注。 那时太小,只觉得有趣。 如今面对这巨大的纸屋,伴着秋雨般淅沥的春雨声,阿诺的心中填满了岁月纷扰的愁思。悠悠经年,岁月早已被这纸预示好了一切。无非是在追悼亡人的路上不断走向被追悼,由元宝的送出者不断变为元宝的受用者,如此尔尔。 这,就是我们的人生啊,多么残缺与忧伤。 静立半晌,外头的雨声竟是慢慢小下去了。灯光晕开窗上的雨迹,看来,明天准会是一个晴天。 江海寄平生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,长复江村事事幽。 自去自来梁上燕,相亲相近水中鸥。 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。 但有故人供禄米,微躯此外更何求? 长夏。临浣花,艺万倾木,结庐枕江。纵酒,吟啸。于杜甫,曾有时光,安若桃源。草堂的生活,闲淡如一尺素的夏日流光,心事可以全部交付给一只水鸟。“微躯此外更何求?”暂时的停靠,让杜甫获得了有家可归的幸福感,他舀江水洗尘,煮粟米暖胃,满足地与老妻下棋。这正是杜甫心之所向的安宁,他一直狂想着一路欢歌一路诗,幻想着以出仕这般入世的方式普渡众人。近人所绘杜甫多神色淒楚,眼前若有寒烟锁住,忧怨沉重地遥望远方。所以,为了自己的一腔“桃源梦”,他宁寄平生于孤舟,“天地一沙鸥”般奔赴远途,毅然丢下现实中美好的一隅。夔州、江陵、洞庭湖……常年乘舟,一路南下。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,年复一年的江面让他心生迷惘,让他骨受湿寒。远方,是迷途?是终点?他真的迷惘,怅然喟叹为何老友纷纷离世,为何自己孤身一人。幸而,“老病有孤舟”,他还有一尺船。船上水上的车,有了船,就可以继续驶下去。杜甫是诗人,是圣哲。古来圣人总是慈悯坚忍到极处,他们不搀杂已利,故而心灵可以更好的贴近大地。众人与已同来源土,终归于土。他们呼号、奔叫、漂泊,他们的眼中沉郁而温软。杜圣让“伟大”“英雄”“不朽”这些词空洞、轻飘、乏于真感,他是站在山谷中深情俯瞰群峰的人。韭菜盒子 王小冬住在城北兴旺街上,出家门,直走,踏出巷子便是一路排的街坊。 正对面的是北记杨梅汁,挺古老的招牌,房子很深,老板爱听扬剧,夏日里悠悠散发出冰凉凉的甜丝。再左边是李家酥饼店,整日油油的气味。右面是杨家香店,很宽敞,安安静静、沉沉迷迷地香着,即便非年非节也有长辈为晚辈抱一些斗香回去,祈祷考试或者出行顺利。 小冬最爱李家的韭菜盒子,从小吃到大的,店家是个大高个子,哑巴,右眼下有颗痣。平日里,小冬总会在放学时买一个,吃不腻的。但不免有贪玩的时候,买了小人书就只剩下几毛钱。哑巴也不恼,伸出大粗手,朝小冬招招手。金色夕阳下,她清楚地望见,白面粉覆盖住他深深的老茧。 小冬一吐舌头,拿了袋子飞也似的奔回家。 邻居张大妈晓得小冬爱这一口,有时买一些韭菜盒子让小冬给教教张小明的算数。小冬其实是愿意的。谁不爱吃脆脆的皮,细细的粉丝,香香的韭菜呢?但张家有只大斑点狗,老用毛蹭小冬。 小冬13岁时发了高烧,天晕地转,几天没起来。好容易醒来,她妈问,吃啥嘞,稀饭就腌萝卜?小冬摇摇头。要不煮些汤圆,小冬不点头。韭菜盒子,她轻轻地说,声音不大,然后又歪头闭眼歇息。 妈妈一会儿就拎了几个韭菜盒子回来,后头跟了李四。几天没见着小冬,估摸她一定是病了,又买了柳橙汁,打了桂花糖糕、核桃酥,怕她嘴巴没什么滋味。见她的小脸瘦了一圈,眼往里面凹。他一颤,摆摆手,意思是他要走了,小冬爸爸倒滚水给他,他指指围裙笑了,意思是店里生意还要人哩。 十多年后,小冬嫁到了大城市,在海边,远远近近都是蓝汪汪的,还有教堂和公园,白鸽子在城市上空盘旋。有了孩子,孩子似乎不爱韭菜盒子,约莫她的兴趣也淡了罢。 后来李四改卖馄饨,据说手艺不减。 新 苗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ehuaf.com/hhwh/539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他往生前两三天说看到粉色的莲花,合掌跟大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