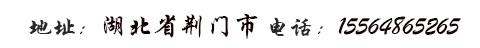迦陵回乡诗生南开为有荷花唤我来
|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10月13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诗生南开》的报道。“年,因为李霁野先生一声召唤,叶先生来到南开讲学。年,因为叶先生一声召唤,我们决定编这本书。”“先生和南开有40多年的缘分,但专门讲述这段师生缘的书几乎没有,这本书填补了一个空白。”坐在南开大学迦陵学舍,捧着这本《为有荷花唤我来——叶嘉莹在南开》,刘学玲和陈焰的语气有些激动。“很多人都说,你是天津人吗?我说不是。那你是南开的校友吗?我说也不是。那中国那么大,那么多学校,你为什么选择了天津的南开大学?”年,叶嘉莹在天津大剧院举办了一场公益讲座,主题是“要见天孙织锦成——我来南开任教的前后因缘”。讲座开头,92岁的老人特意提到了几个常被人问起的问题。那天,刘学玲就坐在台下。几年之后,刘学玲、陈焰和所有参与编写《为有荷花唤我来》一书的南开人一起,试图从学子的角度,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。寻找的过程绝不轻松,但汲汲骎骎一路走下来,这些编写者本身,也成了答案的一部分。师生刘学玲和陈焰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级的同班同学。年10月,南开百年校庆,他们班返校的同学,给南开大学文学院时任院长的老同学沈立岩提了个请求,“能不能让我们见见叶嘉莹先生?”年,时年55岁、离乡30余年的叶嘉莹向教育部申请利用假期自费往返大陆讲学。当年4月,叶嘉莹第一次来到南开,讲诗授词,自此扎根。但开始几年,不是每届学生都能赶上她的课,82级中文系就是擦肩而过的那一批。年10月19日上午,返校的近20位老同学,来到叶嘉莹位于西南村的家中。这群多数未曾谋面的“弟子”向她汇报,他们准备做一本82级中文系纪念图集,要把先生鲐背之年依然给在校生讲诵宋词的图片收录进去。叶嘉莹听后“满怀期冀”地说:“你们出一本我在南开讲学的书给我吧。”“她特别看重自己跟学生之间的情分。”沈立岩觉得,说出这句话,是因为叶先生想知道同学们是怎么看待她这段教书历程的,期待给在南开的教书经历“一个文字的归宿”。老师的一句话,“学生们”放在了心上,“出来就拉了个筹备工作群”。他们将其视为一份“作业”,想用这本书补上那段未能在教室中圆满的师生缘分。因叶嘉莹极爱荷,书名就取自她记写荷花盛开的南开马蹄湖那首诗中的一句,“为有荷花唤我来”。言及自己与南开大学结缘之始,叶嘉莹曾多次在文章和讲座中感念一位前辈:现代著名翻译家、南开大学外语系名誉主任李霁野教授。李先生是叶嘉莹恩师顾随的同事、好友,叶嘉莹以“学生”自称。“当我于年考入当时北平的辅仁大学时,李先生正在辅大西语系任教,而我则只不过是一个才考入学校的国文系的新生。”叶嘉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,青年时代她读过霁老翻译的《简·爱》等小说,但直到年3月,身在台北的叶嘉莹受顾随先生之托,代恩师探望几位任教于台湾大学的故交,她才第一次见到了李霁野先生。那之后,时移世易,台湾白色恐怖愈演愈烈,霁老返回大陆,叶嘉莹在台带着不满周岁的大女儿被拘捕,自此经历了人生中一段艰苦备尝、天涯飘转的岁月。一晃近30年过去,已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的叶嘉莹,从温哥华寄出一封回国教书的申请信,没过多久,她又从报纸上看到了李霁野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。她兴奋地致信李先生,将自己的近况和打算告知师长。年,教育部批准了她的申请,安排她到北京大学授课,一段时间后,叶嘉莹收到了霁老的来信。信中老人诚恳地邀约她转到南开。彼时的叶嘉莹对南开还没有深入的了解,因老师的一声召唤,就离开家乡北京,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……接受采访时,刘学玲反复讲起这段往事,编辑《为有荷花唤我来》的过程,好像一种传承和延续——叶先生对师长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敬爱,成为感召南开后辈倾力做书的力量。拜访叶嘉莹几天后,第一条“征稿启事”被发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校友 叶言材总说他和姑母的性格很不一样,但在刘学玲看来,这对姑侄有着一脉相承的严谨。“叶师兄一再跟我们说,对书稿里的文字、插图,有疑问的地方一定要核对清楚。”而他本人在撰稿过程中,也常常发邮件和姑母确认细节,为了叶家老宅屏门上的“寿”字颜色究竟是红是黑,姑侄俩也会一来一回地“争论”。为什么如此“较真儿”?叶言材告诉记者,他不写便罢,只要写,就要保证事实的准确,那是他对姑母的尊重。为了给先生出这本书,“人家说三审三校,我们三十校也不止。”刘学玲说。书中的照片说明都做了一一考证。为确定一张照片到底是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80年代末拍的,他们多方核实,最终发现,这张多次被引用的照片时间标错了。这样的严谨为叶先生称赞。但也有“挨批”的时候,比如有些第一批征集来的文章被批“没有真情实感”。在汪梦川的师妹黄晓丹的印象里,叶嘉莹尤其看重一件事——真诚。学生评诗,如果只是搬运别人的观点或赶时髦,和自己的生命体验没有关系,不够真诚,先生觉得“不是什么好事情”。韦承金曾把自己创作的几首诗词发给叶嘉莹审阅,先生肯定了他的才华,却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:“我读了你的旧体诗词之后,觉得酬唱的作品太多了,把作品的品格降低了……宁可少作诗,但是要作就一定尽力作出好诗来……要在心里面真正有所感动时才写诗。”现在黄晓丹做研究,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“诚实地表达”。采访中,好几位采访对象特意叮嘱,不要写他们的故事,写叶先生就好,因为不希望夸大了他们的成就,“借着叶先生的光芒抬高自己”。年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演讲。(韦承金摄)师·生“没关系没关系,我要站着讲。”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一直记得初见面时,叶先生对他说的这句话。那是年初,他刚刚赴任,在学校举办的一场春节茶话会上,87岁的叶嘉莹教授坚持起身,向新校长做自我介绍。龚克想让叶先生坐下说,老人不肯。她像上课时一样,站在原地,将自己从加拿大回国来南开讲学的经过娓娓道来。她缓缓吟诵起自己在温哥华向祖国递交申请之时写下的诗句:“向晚幽林独自寻,枝头落日隐余金。”这两句诗一下子打动了龚克,让他至今记忆犹新,“先生在独自寻什么?她肯定不是在寻找回住处的路,而是在寻找归国从教的路”。《为有荷花唤我来》一书的开篇,是叶先生亲撰的《我与荷花及南开的缘分》一文。她在文中夸赞龚克“每次见面经常与我谈论诗词……有一次开会,他走在我的身边竟然还顺口背了我的一些诗作,我对理科出身的领导能对旧体诗词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和修养,实在感到钦佩不已”,龚克却说,自己不会作诗,是叶先生一身“文气”、起身讲诵、兴发感动的师者风范感染了他。“先生要站着讲”——几乎每个采访对象都会和记者提到这一点,也包括给本书作序的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教授。年叶嘉莹第一次授课结束,临行之际,当时还在中文系读研究生的陈洪为先生整理了行李。20世纪90年代,叶嘉莹创立研究所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波折,也是在陈洪出任中文系主任后,与各方合力推动,事情逐渐有了转机。“30多年来陈先生亲眼看到了我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。”叶嘉莹在《我与荷花及南开的缘分》中写道。作为同行,一路走来,陈洪也对叶嘉莹“年过九十,站着讲两个小时诗词”的风采钦佩不已,他觉得那是叶先生对学生、对诗词、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重。“说起来都惭愧,我一过了七十岁,就总坐着讲了。”但在南开师生眼中,自叹惭愧的陈洪与叶先生有着相同的师者之风。“陈洪先生给很多届本科生讲过大学语文这门基础课,后来也一直带着我们这些后辈教师讲大学语文,还拿到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。”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静说,南开学风鼓励老师以讲台为重,有一种“培育好老师的空气和土壤”,“好像大家都有种使命感,觉得做老师的立足点应该是先把课上好,只做文献是远远不够的”。张静师从叶嘉莹多年。她在《为有荷花唤我来》中撰写了一篇名为《望日莲》的文章。望日莲是向日葵的别称。叶嘉莹在南开40余载,不只她的学生,她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,甚至“粉丝”,很多都成为老师。他们就像是一朵朵望日莲,无论被栽植到哪一片土地上,都始终望着启迪心智的光芒照来的方向,结出沉甸甸的种子。叶言材在日本大学任教几十年,他发现自己为师、为学的风格受到了姑母潜移默化的影响——姑母“偏爱”上大课,他自己也如此。他教日本学生中文,最喜欢上的课是最基础的“会话”,即日常汉语对话。这显然不是一门能出论文、出成果的课,但叶言材不在意,他觉得,“既然他们要学习中国文化,那就必须把基础打牢靠。我是中国人,又是南开中文系出身的,我有责任告诉他们原汁原味的中文是什么样的,要把中国文化真正的魅力展现给这些学生。”张静至今记得,自己第一次踏上讲台前,在家里“排练”了好几遍,心里始终有个困惑:正式面对学生时,要不要照本宣科?“我们成长路上经历过不同的老师,有的可能就是照本宣科;有的就像叶先生,有充分准备,没有稿子,天马行空,启发学子的心灵。”张静说,对于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,前一种更容易,可她思来想去,还是决心做足准备,放下讲稿。老师的影响不仅在课堂上。年,还在上大三的赵季帮助叶嘉莹整理《论柳永词》的讲座录音。文章随后在《南开学报》发表,成为叶嘉莹在中国大陆学术期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。文章末尾,叶嘉莹特意署明“整理者:赵季(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)”,并托人转交一百多元的整理费,赵季坚决不收。为此,叶嘉莹把他叫到天津第一饭店吃了一顿便饭,郑重地把整理费交给他,“这是你业余时间的劳动,你必须收下”。“这个场面像照片一样一直印在我脑海中。”72岁的赵季说。毕业后,赵季留校任教,桃李天下。直到现在,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,只要是学生业余时间帮助录入或校对,他都一定按字数或时间付给学生费用。著作出版时,他也一定会在后记中说明哪些学生从事了哪些相关工作。诗·生播下种子的人——这是陈洪对叶嘉莹的形容。她一生传承中华诗教,播种师心,也播种诗心。“陈省身先生是大数学家,也在叶先生的带动下提笔写古体诗。”叶嘉莹八十岁寿辰时,常来听她讲课的陈省身为她赋诗贺寿,写下“锦瑟无端八十弦,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归去来兮陶亮赋,西风帘卷清照词。”陈洪觉得,这就是叶嘉莹的魅力,“不见得马上就能看出怎么样,但她的影响在那儿。”“书生报国成何计”的拳拳心迹,早已在马蹄湖畔写下了答案。为激励南开大学的学生学习古典诗词,年,叶嘉莹用自己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金的一半设立了“驼庵奖学金”,一年一度,延续至今。考试内容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汉魏六朝诗选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唐宋名家词选》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。最初一等奖奖金为两千元,近年增至一万元。奖学金开始只面向中文系学生。赵季向叶嘉莹提议,很多文理兼优的学生,在高考时被动选择了理工科,其实他们的古典诗词水平很高,热情也很高。叶嘉莹欣然同意。现在,“驼庵奖学金”已在南开铺开,许多理工科学生获奖。年,叶嘉莹又在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“迦陵基金”,目前已完成了前期捐赠余万元,用于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。沈立岩感到,一种氛围正在形成,“南开从上到下诗学的意识越来越强烈”。南开大学图书馆里,叶嘉莹的书不知被“翻烂了”几套。她的讲座或公开课,晚上7点开始,下午4点多就开始排队,讲座每次都安排在最大的主楼小礼堂,还是装不下。迦陵学舍成了学子们的“打卡地”,每年开放日,领票的学生总要排长龙。“办教育不光是在课堂上讲,要整体形成一种氛围。”曾见证着迦陵学舍从图纸到建成的龚克提起了南开校歌,“美哉大仁,智勇真纯,以铸以陶,文质彬彬”。“‘以铸以陶’用什么呢?就是整个校园文化。不是所有南开的学生都听过叶先生讲诗词,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记住叶先生写的每一首诗,但她的到来、迦陵学舍的落成、中国古典文化氛围的兴起,陶冶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,不管自己能不能做诗人,都愿意读诗词、欣赏诗词、尊重诗词包含的文化。我们希望能把这个留在校园。”龚克说。最近,韦承金正着手把自己20年来在南开听讲座的札记、写过的学人散文整理出来,集成两册书,“我没想过能不能出版,只是想像先生传承诗词一样,把南开的学风和文脉,通过这些文章传承下去”。他将编订好的目录转呈给叶先生,先生非常开心,提了八个字:学者有师,斯文有传。叶言材几乎每年都会在姑母庆祝生辰时送上一份礼物。今年,他用自己的退休金,为姑母塑了一座白铜制的全身像,凝筑她回国40余年,站在三尺讲台传承中华诗教的风采。铜像参考了叶先生最为大众熟知的形象——长身玉立,一条轻盈的素色纱巾垂在身前,右手自然地向外挥到一侧,手指微伸,动作神态像是在讲解板书,传授诗词。年《为有荷花唤我来》出版。“这本书是我跟南开的老师,跟所有听讲的南开同学之间的一个纪念。”叶嘉莹专门为此录了一段视频,她披着荷花披肩,又诵起自己那首诗:“结缘卅载在南开,为有荷花唤我来。修到马蹄湖畔住,托身从此永无乖。”编委会的成员们,看到这里几乎落泪。他们想起叶先生在书的开篇写下的一段话:“记得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篇考古的文章,文章记述在一座汉代古墓中发现几颗千年以上的莲子,经人们尝试种植以后,竟然也生长出来了新一代的莲叶和莲花。夫禅宗有传灯之喻,教学有传薪之说,则我虽老去,而来者无穷,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岂不正在于是。”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ehuaf.com/hhhy/1326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新华社镜头下的夏日济南荷花盛开绘生态美景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